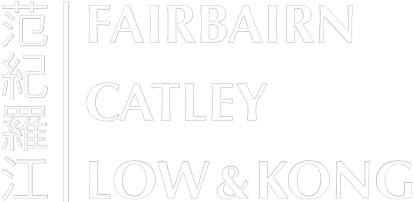中國內地與香港之間的跨境破產程序經常面對獨特而複雜的挑戰。近期的香港案例強調了這一領域的特殊性,並對香港法院在處理承認內地破產程序和協助內地法院任命的管理人的申請時所持的一致做法提供了更深入的解說。
在Re China Electronics Leasing Company Ltd(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内地清算中)(2024年11月28日,HCMP 1676/2024)[2024] HKCFI 3457一案中,北京市第三中級人民法院(「北京法院」)任命的管理人就一家在中國內地註冊的公司向香港法院提出了單方面申請(ex parte application)。該公司並非在香港清盤的公司,即《公司(清盤及雜項條款)條例》(第32章)的條款不適用,因此該申請是根據香港法院的固有司法管轄權提出。
Re China Electronics Leasing Company Ltd一案引用了Re Guangdong Overseas Construction Corporation (In Liq) [2023] 3 HKLRD 262案例第17段所總結有關承認外國破產程序和協助外國管理人的法律原則:
- 依據普通法,法院承認和協助外國管理人的權力並不取決於協助的法院已對公司展開清盤程序,而是依據國際私法原則,取決於法院承認在公司註冊地被任命的管理人為公司的合法代理人這一點。
- 申請人必須使法院確信:
(a) 外國破產程序為集體破產程序,包括在大陸法管轄區啟動之程序;
(b) 外國破產程序在公司的主要利益中心所在的司法管轄區進行;以及
(c) 協助外國清盤程序的管理或協助管理人履行職能是必要的,且該命令與協助法院的實體法和公共政策一致,因此不適用於其他方案所應涉及的目的。 - 至於向管理人提供協助的範圍和條件,相關案例顯示,法院曾向外國管理人提供以下方面的協助,包括 (a) 控制公司的資產;(b) 擱置針對公司資產的本地法律程序;以及 (c) 向第三方取得及收集與該公司有關的資料和文件。
事實上,根據最高人民法院與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於2021年5月14日達成的共識,香港法院與內地法院已在三份主要文件下建立了一個跨境破產程序的相互承認和協助的合作機制(統稱為「合作機制」):
- 於2021年5月14日簽訂的《最高人民法院與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關於相互承認及協助內地與香港特別行政區法院破產(清算)程序的會議記錄》(「會議記錄」);
- 《最高人民法院關於推動香港特別行政區破產(清算)程序承認與協助試點措施的意見》(「最高人民法院意見」),該意見訂明香港法院委任的管理人就香港破產程序向內地三個試點地區(上海、廈門和深圳)法院尋求承認與協助的法律程序;及
- 《內地管理人向香港特別行政區法院申請承認與協助的程序——實用指南》(「實用指南」)概述了內地管理人向香港法院申請承認與協助內地破產程序的步驟。
然而,正如近期多宗案例(例如 Re Guangdong Overseas 及 Re銀河天成集團有限管理人 (01/08/2024, HCMP 658/2024) [2024] HKCFI 2016)所強調,上述合作機制下的文件僅提供了協助的基本框架,並未授予香港法院額外的權力。
這一點在Re China Electronics Leasing Company Ltd案中也得到確認。在該案中,提出協助請求的是北京法院,而北京法院並非合作機制試點地區的法院。香港法院再次表示「非互惠性」不會成為妨礙承認和協助另一司法管轄區破產程序的權力在香港行使的因素。根據普通法,互惠性並非承認和協助的必要條件,至於試點地區以外的法院是否適宜申請承認和協助的問題,應由內地法院處理(Re HNA Group Co., Ltd [2021] HKCFI 2897, §9;Re Guangdong Overseas, §§19-20)。換言之,香港法院承認和協助由另一司法管轄區的法院在香港委任的管理人的權力源自普通法,香港法院會衡量申請人是否有滿足承認和協助的標準(Re Guangdong Overseas, §21)。
在Re China Electronics Leasing Company Ltd一案中,儘管管理人在申請承認及協助方面存在相當長及不合理的延誤(自請求函首次批出後已超過三年才提出申請),而且香港有關銀行對仍為清盤中的內地公司持有信貸結餘的立場並不明確;但法院最終裁定在香港作出所尋求的命令符合債權人的利益。雖然如此,當事人和執業律師仍需注意,香港法院日後希望另一司法管轄區的法院所指定的管理人在發出請求函後不久即迅速採取行動,並僅在必要時(例如有關銀行已表明立場等)向香港法院提出承認和協助申請。
本行在處理跨境訴訟和破產事務方面經驗豐富。如果您對此事有任何疑問或需要相關法律協助,歡迎與我們聯絡。